從2013年《春夢(mèng)》亮相鹿特丹電影節(jié)開(kāi)始,到2019年《春潮》獲得國(guó)內(nèi)外觀眾與學(xué)界的矚目,再到《媽媽!》(原名《春歌》)今年“中秋檔”的如期上映,橫跨將近十年,楊荔鈉導(dǎo)演的“女性三部曲”畫上了句號(hào)。相比《春夢(mèng)》中的強(qiáng)烈欲望和女兒出意外的生命“撞擊”,以及《春潮》中母女之間的激烈矛盾與沖擊,楊荔鈉在“終曲”《媽媽!》中,將一切關(guān)于母女或好或壞的歷史與記憶都以阿爾茲海默癥的方式“遺失”,走向愛(ài)與和解。
 【資料圖】
【資料圖】
疾病帶來(lái)的記憶遺失
老年人的疾病總是不可避免,電影開(kāi)頭的疾病指向的是吳彥姝所飾演的85歲的媽媽——不僅有老年人常患的慢性心血管疾病,還有“老年疑心病”。然而,媽媽的疾病對(duì)于電影來(lái)說(shuō)只是母女關(guān)系的背景交代,觀眾看到,媽媽吃飯需要女兒搖鈴鐺喚起,溝通方式是寫便箋——這些細(xì)節(jié)中呈現(xiàn)的都是母女之間的某種未打開(kāi)的心結(jié)。
直到由奚美娟飾演的65歲女兒發(fā)現(xiàn)自己患上阿爾茲海默癥,母女關(guān)系僵硬的因由及其更大的時(shí)代或歷史背景慢慢呈現(xiàn)出來(lái)。不同于《困在時(shí)間里的父親》(佛羅萊恩·澤勒,2020)直接將阿爾茲海默癥作為電影重復(fù)記憶碎片的感官手法,盡管《媽媽!》在片尾給出對(duì)老年群體和阿爾茲海默癥的關(guān)注,但電影中女兒的疾病其實(shí)有著極強(qiáng)的敘事“工具”價(jià)值。
長(zhǎng)期以來(lái),在家里,女兒要打理好一切,照顧好退休二十年母親的生活,根據(jù)母親和自己不同的飲食習(xí)慣做好飯,每天對(duì)她進(jìn)行“清洗”。在外面,她是養(yǎng)老院的志愿者、定期掃大街的義工,遭受到文淇所飾演的小偷女孩周夏栽贓后,卻會(huì)主動(dòng)替陌生人“頂罪”,即便家里被周夏盜竊,也要將她救出來(lái)。如果沒(méi)有阿爾茲海默癥的到來(lái),興許母女關(guān)系的“冰層”不會(huì)打破,女兒那些“清教徒”般行動(dòng)的動(dòng)機(jī)也無(wú)從得知。
因此,從故事的邏輯性上來(lái)說(shuō),女兒的患病既包含著她長(zhǎng)期食素的醫(yī)學(xué)因素,也包含著記憶中所背負(fù)的“罪責(zé)”造成的精神壓力,更涵蓋著電影敘事推動(dòng)的要求——疾病成為揭開(kāi)歷史或記憶真相的缺口,正如多年前的公益廣告詞“他忘記了很多事情,但他從未忘記愛(ài)你”,對(duì)應(yīng)著阿爾茲海默癥題材文藝作品中常見(jiàn)的“有所忘、有所不忘”的模式。《媽媽!》中的女兒忘記的是回家的路、眼前的母親,但記憶遺失并不是電影的重點(diǎn),而在于其對(duì)女兒內(nèi)心愧疚的強(qiáng)化及其背后歷史真相的揭示與剝離。
老年母女的愛(ài)與慈悲
在電影的前半部分,觀眾大多可見(jiàn)的是終身未嫁的女兒對(duì)母親的“規(guī)訓(xùn)”,是一種“由下而上”的贍養(yǎng)義務(wù)表述。反過(guò)來(lái)看母親的“叛逆”,其實(shí)是對(duì)女兒的回應(yīng)。面對(duì)女兒的“爬太高會(huì)摔死”,她反擊“不爬也會(huì)死”;女兒不讓自己抱野貓,她會(huì)說(shuō)女兒“一輩子浪費(fèi)了很多水”;女兒“不太關(guān)心自己”,她會(huì)假裝半夜暈倒在地上;女兒生氣打自己,她要打回去。這個(gè)“可愛(ài)”的母親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成為了女兒的“女兒”,二十年的退休歲月中,母親已然與女兒實(shí)現(xiàn)了一次角色的轉(zhuǎn)換,在此期間,母親是以“女兒”的方式愛(ài)著自己的女兒。
阿爾茲海默癥的到來(lái)在無(wú)形中又將母女之間的角色進(jìn)行了“再轉(zhuǎn)置”。這層角色的“再轉(zhuǎn)置”開(kāi)始于女兒初患病后,夜里做義工沒(méi)找到回家的路、母親坐在家門口等到早上五點(diǎn)的那天。盡管她此時(shí)還沒(méi)注意到女兒已經(jīng)患病,但坐門口等待長(zhǎng)夜未歸的子女,就是天下所有母親都會(huì)完成的“使命”。而女兒在得知自己將會(huì)忘記一切后,盡快地將財(cái)產(chǎn)、保險(xiǎn)全部轉(zhuǎn)到了母親名下,讓母親和她此后的生活能有更好的保障。母親不愿意住養(yǎng)老院以“作妖”的方式回到家,女兒便心平氣和地把自己的病和盤托出,將自己再次交給母親。
由此我們不得不懷疑,母親在過(guò)往的時(shí)間中,不過(guò)是與她的女兒在玩著“家長(zhǎng)與孩子”的游戲;當(dāng)她得知了女兒患病,順其自然地重新接手了“母親”的角色——她其實(shí)完全可以在照顧好自己的同時(shí),照顧好那個(gè)生病的女兒。此后必然要有漫長(zhǎng)的歲月,既有女兒的記憶慢慢剝離出的歷史真相,她不得不面對(duì)多年已然“自我治愈”的“傷疤”,也有“即上而下”的慈悲、包容與原諒。電影中可見(jiàn),因?yàn)樗ダ希赣H其實(shí)早已力不從心,帕金森也“預(yù)約”了她接下來(lái)的時(shí)間,但她依然要“堅(jiān)挺”到最后一刻,反諷著“久病床前無(wú)孝子”的凄涼。
跨越代際的和解與救贖
與《春夢(mèng)》《春潮》類似,楊荔鈉在《媽媽!》中也大量使用了手持搖晃鏡頭。本片中這種搖晃除了是對(duì)女兒愧疚不安內(nèi)心以及阿爾茲海默癥帶來(lái)精神不安的視覺(jué)呈現(xiàn)外,其實(shí)還有楊荔鈉導(dǎo)演“女性三部曲”將“水”作為審美載體和文化聯(lián)想的一以貫之,鏡頭的搖晃正如波動(dòng)的水面,任何一顆石子的到來(lái)都必然蕩起漣漪或浪花。《春潮》中的女兒在母親病床前,將自己對(duì)母親的怨念留了長(zhǎng)長(zhǎng)的獨(dú)白,東北地區(qū)消融的冰雪也暗涌漫流直至匯入江海,其所建構(gòu)的是女性的生命之潮。到了《媽媽!》,如果說(shuō)電影前半段的手持搖晃鏡頭預(yù)示著人物關(guān)系的轉(zhuǎn)變,那么到了后半段,直到最終母女到達(dá)海邊,鏡頭逐漸平穩(wěn),看似海水漲潮、浪花涌動(dòng),女兒卻在母親引導(dǎo)自己學(xué)走路(就像小時(shí)候一樣)的時(shí)刻,同時(shí)走向的是彼此真正的和解。
歷史的真相被剝離出來(lái)后總是呈現(xiàn)著血色,個(gè)人的命運(yùn)再?gòu)?qiáng)大也難以抵御時(shí)代或歷史的推動(dòng)力,隨波逐流帶來(lái)的后果必然需要一生的自我救贖。盡管病情逐漸加重,女兒依然完成了父親考古日記的整理工作。如同電影中的詩(shī)歌:“媽媽是海,我是一滴水,爸爸是一條不會(huì)游泳的鯨魚。”活在女兒記憶與愧疚中的父親,可能長(zhǎng)期都是女兒乃至于母親的精神支柱。女兒對(duì)周夏的救贖,也預(yù)示著她與自身的和解,在代際的跨越中傳承著慈悲與包容。
不過(guò),在楊荔鈉的“女性三部曲”中,《春夢(mèng)》的主角方蕾是家庭優(yōu)渥的全職太太,《春潮》中的母親是干部、女兒是記者,到了《媽媽!》,母女倆都成為了大學(xué)教授。如果說(shuō)前兩部的人物還能或多或少與普通觀眾產(chǎn)生聯(lián)系的話,《媽媽!》則顯然與平民大眾拉開(kāi)了較大的距離,角色的語(yǔ)言與行動(dòng)較難讓大眾產(chǎn)生共情。不可否認(rèn)的是,正像導(dǎo)演楊荔鈉所說(shuō):“海浪象征母愛(ài)的力量也代表人生的浪潮,反之,大海也同樣以她的胸懷擁抱世間所有熱愛(ài)她的生靈。”《媽媽!》中女兒的自我和解,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(shuō)是楊荔鈉與世界的和解;父母子女之間的愛(ài)、慈悲、和解與救贖,無(wú)關(guān)時(shí)代、階層、學(xué)歷與職業(yè),它是長(zhǎng)久共通的存在。(張仕林)
關(guān)鍵詞: 母女關(guān)系 回家的路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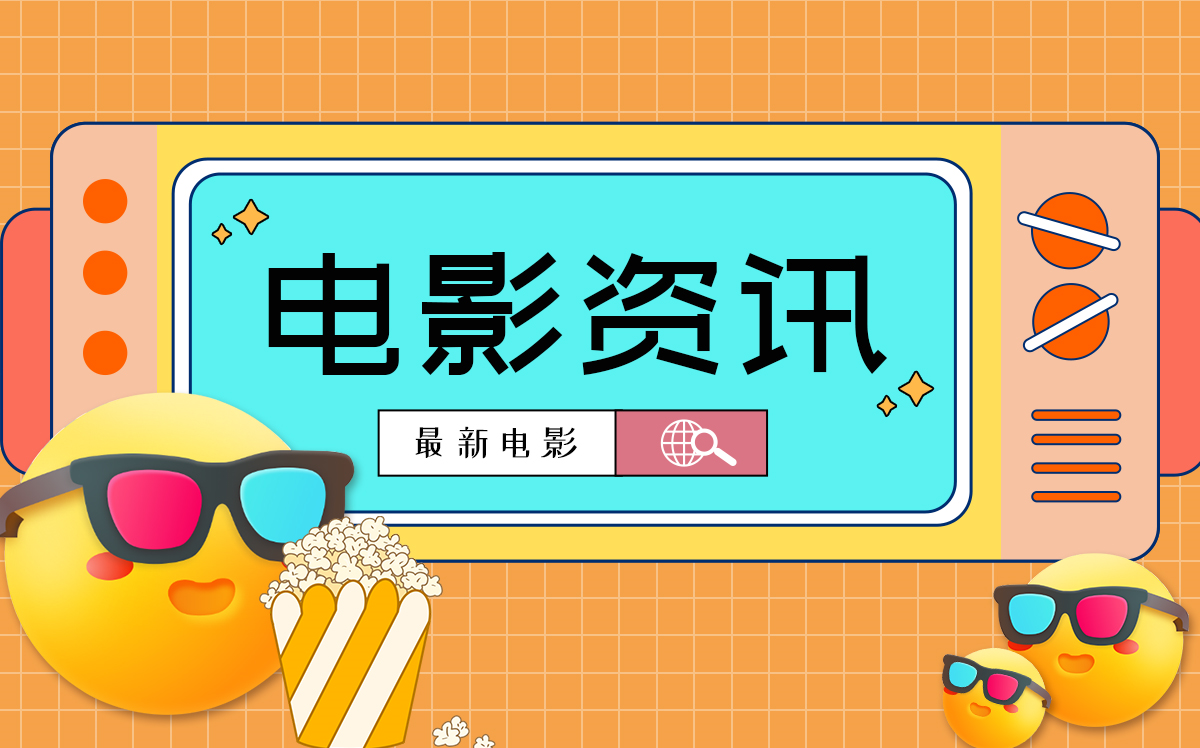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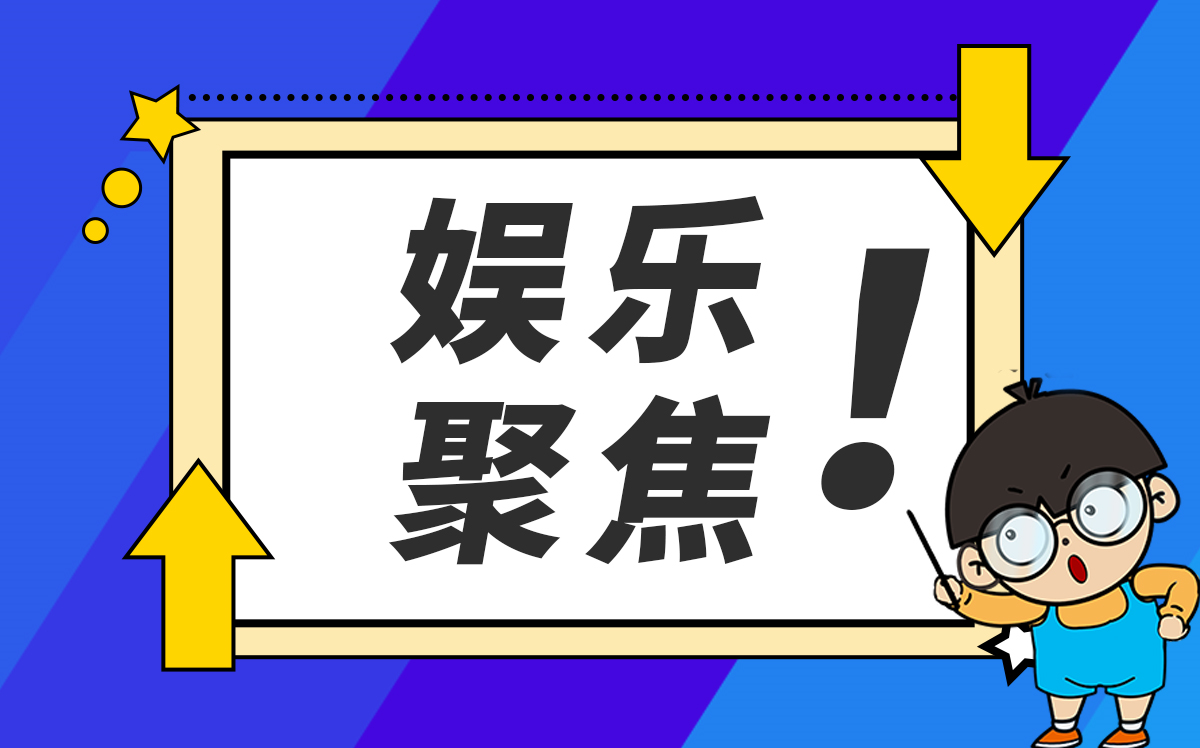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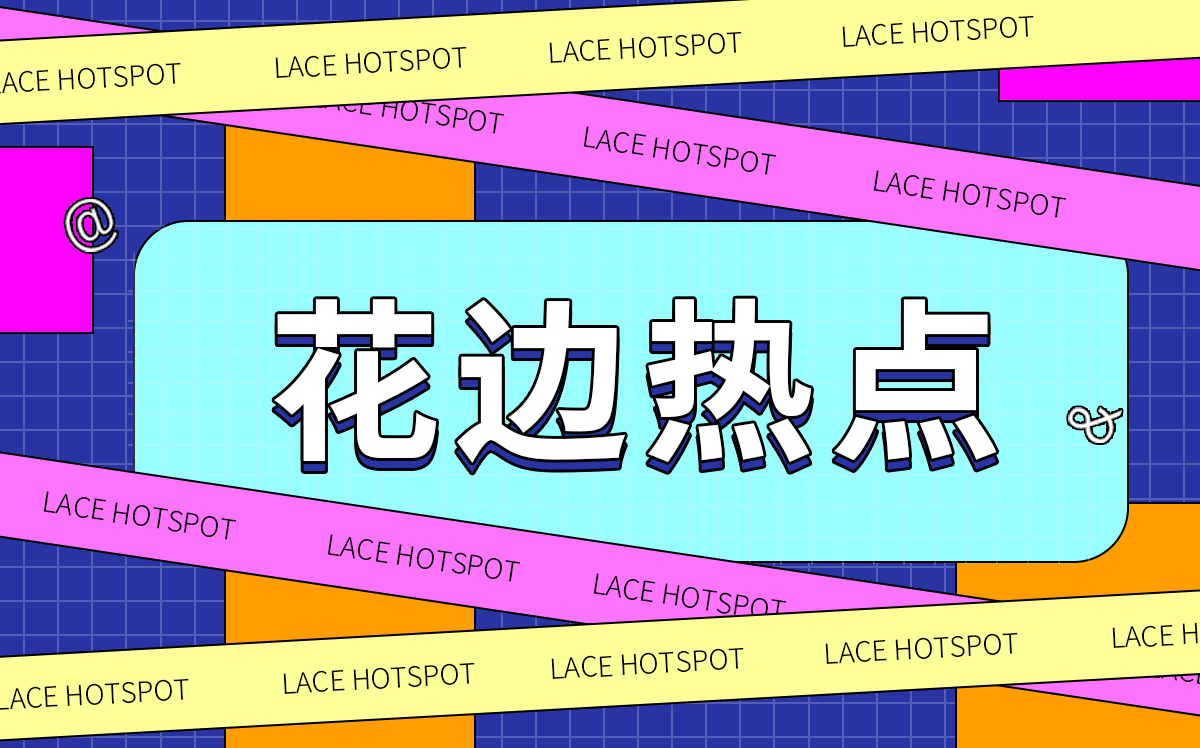


 營(yíng)業(yè)執(zhí)照公示信息
營(yíng)業(yè)執(zhí)照公示信息